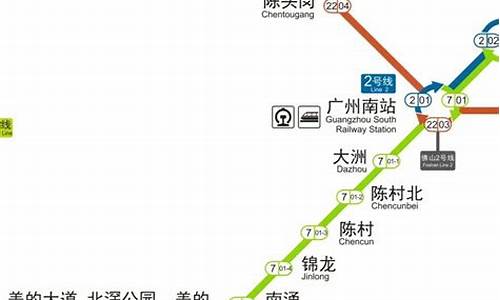突厥斯坦游记攻略_突厥斯坦共和国现状

伊斯兰教著述中有两个起儿漫(克尔曼,Kerman),一个在中亚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之间, 其城今仍存在, 名曰起儿漫内(Kermaneh),即《辽史·天祚本纪》之起儿漫;另一个在波斯南部,即《西使记》之乞尔弯,《辍耕录》卷七回回石头条之乞里马泥,《明史》之乞力麻儿,今濒临波斯湾之克尔曼。 该起儿漫“北部属于波斯高原,地势甚高,其中有高山系以间之。西南抵波斯湾……起儿漫雨量甚少,然在冬季,山上积雪甚厚,山高,积雪几经年不化”。
《辽史·天祚记》记载1141 年发生的卡特万战役时说:“三军惧进,忽儿珊大败,僵尸数十里。驻军寻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国王来降,贡方物。又西至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号葛尔罕。” 这段记载显然颠倒了事实。首先,耶律大石以“甲辰岁”即位,即1124 年,而不是在卡特万战役后的1141 年。其次,保大四年(1124 年),耶律大石在今外蒙鄂尔浑河辽镇州可敦城召集北边七州十八部大会,“遂得精兵万余,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 尚不可能在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之间的起儿漫这样一个小镇称帝即位。《辽史》之所以提到起儿漫,作者认为,它可能将波斯南部之起儿漫的哈剌契丹王朝与耶律大石建立的哈剌契丹王朝弄混淆了。正如多桑所说:“突厥斯坦与起儿漫有两个哈剌契丹王朝,后一王朝晚于前一王朝一百多年”。 起儿漫王朝的建立者是八剌黑。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八剌黑及其弟哈迷的不儿均为哈剌契丹人。在西辽统治时期,哈迷的不儿曾多次奉命出使花剌子模。1210 年,西辽在塔拉斯败于花剌子模沙摩诃末以后, 八剌黑和哈迷的不儿与西辽守将塔阳古同被俘。之后,兄弟两人受到花剌子模沙的信任,八剌黑被封为哈只不,哈迷的不儿逐渐成为一名异密。 八剌黑初仕于摩诃末,继又仕于其子该牙思丁,被任命为伊斯法罕统兵官。
在蒙古军西征,花剌子模沙摩诃末败亡之时,该牙思丁的部下都属望于逃奔印度的扎兰丁,在这种形势下,八剌黑又与该牙思丁的丞相塔术丁迦里不沙尔吉不和, 他征得该牙思丁的允许奔赴伊斯法罕, 准备取道起儿漫去印度投奔扎兰丁。1224 年,八剌黑来到起儿漫的古瓦希尔堡,该堡领主叔扎丁阿布勒哈辛动员五六千人进攻八剌黑的军队。八剌黑迎战,攻克其城堡,但内城仍被叔扎丁之子占领。起儿漫已于回历607年(1210 年—1211 年)归并花剌子模朝。这时,扎兰丁从印度前来,八剌黑向他表示忠心,并把女儿献给他。扎兰丁召见叔扎丁之子使其献出内城。
八剌黑已改变去印度的主意,准备长期占据起儿漫,建立哈剌契丹人的王朝,因此他极力想摆脱扎兰丁的控制。“扎兰丁留此城月余,听说博剌克有叛意,统将斡儿汗劝王先据其人而夺其地。可是王相火者吉罕以为判形未著,不宜惩罚首先归命之诸侯,致失人心。” 扎兰丁在起儿漫作短暂停留后前往法尔斯。行前,他让八剌黑随行共商进攻波斯大计。八剌黑则装病拒绝出城去见扎兰丁,扎兰丁因忙于北上去波斯,只好同意八剌黑留在起儿漫。从这时起,八剌黑就在起儿漫建立了一个历时八十多年的哈剌契丹王朝(1224 年—1306 年)。 起儿漫王朝与蒙古帝国最早建立联系是在八剌黑时期。八剌黑建立起儿漫王朝后, 首要任务就是摆脱和消灭花剌子模的残余势力。回历624 年(1226 年-1227 年)扎兰丁从印度经起儿漫来到伊剌克,与该牙思丁发生矛盾。该牙思丁于是派急使到起儿漫邀见八剌黑,他们之间达成协议,约定八剌黑到阿巴儿忽里草原迎接他。八剌黑在该牙思丁到达起儿漫不久便杀死了他,并向蒙古大汗报告说:“你们有两个敌人:扎兰丁与吉牙撒丁。我把一个的头送来给你们。” 八剌黑通过消灭花剌子模的部分残余势力巩固了政权,同时也讨好了蒙古大汗。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将领塔亦儿·把秃儿围攻昔思田(今伊朗东部之锡斯坦),各异密遣使八剌黑要他投诚,并让他出兵援助围攻。“八剌黑发现权势是在成吉思汗后人的手里,因此他接受命令,表示归顺。”
自此之后, 起儿漫王朝接受蒙古大汗和伊儿汗国诸汗的统治而成为蒙古汗国的属国。可以说,起儿漫王朝的统治史也即它与蒙古汗国的关系史。关于两者的关系,由于史料有限,大多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起儿漫王朝的王位不是世系继承,而是由蒙古大汗任命。蒙哥汗以后,则由伊儿汗国诸汗来任命。除了开国者八剌黑得到哈里发赐予的忽都鲁算端的称号外, 他之后的王位都要得到蒙古汗国的任命和批准。如八剌黑之子鲁克那丁的王位由窝阔台汗任命, 忽都不丁取代其堂弟鲁克那丁得到蒙哥汗的批准、乞合都汗立帕的沙·哈敦为起儿漫王等。起儿漫王朝归顺蒙古大汗后,窝阔台汗命令八剌黑入朝召见,八剌黑以年老婉辞,另派其子鲁克那丁前往哈剌和林去朝谒窝阔台汗。鲁克那丁在回历六三二年(1235 年,或稍早)前往大汗首府,途中得知其父八剌黑死去(死于1235 年7、8 月间)及其堂兄忽都不丁继立的消息。但他没有返回,直抵哈剌和林大汗宫廷,因为鲁克那丁是起儿漫王朝第一个入朝者,所以窝阔台汗将起儿漫的国土赐给他,并下诏让他承袭其父忽都鲁算端的称号,又下令命忽都不丁入朝见蒙古大汗。鲁克那丁遂返回起儿漫就任。忽都不丁来到和林后,先是侍奉窝阔台汗,后被派到中国,在丞相马合木·牙老瓦赤手下供职。在贵由汗时期,忽都不丁曾活动想返回起儿漫夺取鲁克那丁的算端之位,但其师傅镇海反对,故忽都不丁只得仍随牙老瓦赤留在中国。而“鲁克那丁仍拥有起儿漫的国土,并把定额贡赋,如巴里失和骆驼缴纳给征收的异密,直至蒙哥可汗荣登帝国的宝座。”拉施特评价鲁克那丁说:“起儿漫的算端是鲁克纳丁,他创立了公正裁判并表现得很公正,任何非常事件也没有发生过。”
贵由汗死后,政权转到拖雷系的蒙哥汗手中。这一政局的转变在起儿漫也有反映。正在中国的忽都不丁随同丞相牙老瓦赤入朝面见蒙哥汗, 大汗对他甚为宠爱, 封他为起儿漫算端,并派一名蒙古人作为监护他的八思哈(意为“镇守者”)随他返回起儿漫即位。一行人到达也里(今阿富汗西北境赫拉特)时,忽都不丁遣使先行至鲁克那丁那里,传宣诏命,并召其入朝。鲁克那丁得知世道已变,于回历650 年剌马赞月(1252年12 月—1253 年1 月)出发前往罗耳斯坦(今伊朗西部鲁里斯坦),之后前往汗廷见蒙哥汗。1253 年10 月至11 月,从蒙古返回的历史家志费尼在路上遇见他。鲁克那丁到达汗廷后被处死,忽都不丁就正式取得了起儿漫王位。
起儿漫王朝的最后一个统治者沙只罕于1303 年受合赞汗册封嗣位,“然有人诉其不敬汗使,岁贡不时,虐待其国中贵人。完者都(1304 年~1316 年在位)征之入朝,见其年幼貌善,宥其罪。然留不遣,命蒙古官代治其国。沙只罕后退居泄剌失(伊朗设拉子市)城,聚积货财,亦颇有权势,遂终于是城。是为1223 年来君临起儿漫哈剌契丹朝末主之结局”。正如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所说:“起儿漫,是波斯境内之一国。昔日国王世袭,自经鞑靼侵略以后,世袭之制遂废。鞑靼遣其乐意之王治之”。
第二,蒙古汗国委派蒙古人作为监督官管理起儿漫王朝。马可波罗说:“自从划归鞑靼人的版图以来, 就由鞑靼人委派的监督官进行管理”。忽都不丁由中国返回起儿漫继承王位时,蒙哥汗就曾派一名蒙古人作为监护他的八思哈。此外,蒙古汗国还向起儿漫王国派驻军队。合赞汗时期,“让忽剌术万人队开往法儿思和起儿漫境内,一旦需要,就让他与异密答速黑和起儿漫算端会合在一起”。
第三,起儿漫王朝与蒙古汗国保持联姻关系。这种联姻多发生在起儿漫王朝中后期,即在伊儿汗国时期。如忽特鲁格秃儿罕之女帕的沙·哈敦曾先后嫁给阿八哈汗和乞合都汗;帕的沙·哈敦的兄弟,扎兰丁·苏尔合忒迷失之女沙·阿蓝嫁给拜都汗。
第四,起儿漫王朝统治者曾多次向蒙古汗国朝贡。如上文所述,鲁克那丁执政时期,每年向蒙古汗廷缴纳定额的巴里失和骆驼,以为贡赋。忽都不丁“将四周国土征服后,屡次入朝伊儿汗国面见旭烈兀汗,备受恩渥。” 自八剌黑投靠蒙古大汗后, 起儿漫王朝成为蒙古汗国的属国,从而使起儿漫百姓免遭战火的涂炭。此外,哈剌契丹人来到起儿漫地区后很快接受了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法规,同时也把他们自己的经济、文化带到了起儿漫,彼此相互借鉴、相互融合。这些都使得起儿漫地区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据《马可波罗行记》记载,“此国出产名曰突厥玉之宝石甚多,产于山中,采自某种岩石之内。亦有不少钢及‘翁尼塔克’之矿脉。居民善制骑士军装,如马圈、马鞍、靴刺、剑、弓等物,手艺甚巧,皆适于用。妇女善于女红,善为各色刺绣,绣成鸟、兽、树、花及其他装饰。并为贵人绣帐幕,其妙不可思议。亦绣椅垫、枕、被及其他诸物。”
起儿漫王朝自行发行货币。拉施特说,至合赞汗止,起儿漫等地以当地的篾力和算端的名字铸币,成色不一。起儿漫王朝的属地忽鲁模思(霍尔木兹)城,其港口是印度各地经营香料、药材、宝石、珍珠、金线织物、象牙和其他商品的商人的汇合地。这些商人将上述商品转卖给其他商人,由他们再远销世界各地,所以忽鲁模思城享有商业之城的盛名。
在宗教信仰上,起儿漫地区的原住居民信奉伊斯兰教。《马可波罗游记》说到,忽鲁模思城的居民是撒拉逊人,肤色暗褐,全部信仰穆罕穆德。哈剌契丹人来到起儿漫地区后很快改宗伊斯兰教。八剌黑在巩固政权后,遣使去谒见哈里发,申明他改宗伊斯兰教,请求封以算端称号。哈里发满足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得到忽都鲁算端的尊称。 作为西辽王朝的延续, 起儿漫王朝是蒙古西征和花剌子模灭亡这一特定形势下的产物, 也是契丹人建立的最后一个政权。起儿漫王朝被蒙古官吏接管后,该王朝便从哈剌契丹人转入蒙古人手中, 而此时的哈剌契丹人也逐渐融入到了当地穆斯林居民中。
马可书中最有趣的描述之一是他勾画的中国南北两地经济活动的图画:中国北方,他继续称为契丹(该名来自原契丹人);中国南方,原来的宋王朝,他称为蛮子。从他的书中,我们知道了在中国北方已经开采煤矿。“从山上矿层中开采的一种黑石头,像木头一样地燃烧,它们很好烧,以致整个契丹不烧其他燃料。”水路的运用同样使他吃惊,他尤其提到了中国经济的主动脉长江在商业上的重要性。“这条河上往来的船只和运载的货物比基督教世界中的任何一条河和任何一个海都要多。”他还说,“每年沿该河而上的船就有20万条,更不用说顺水而下的船只了。”他还提到了帝国运河的经济作用,这条运河是忽必烈时彻底凿通的,经这条运河,大米可以从长江下游运到北京。
为管理繁荣的国内商业和开展与印度、东南亚的贸易,在中国中部港口和广州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商会。这些商会可以与佛兰德尔的行会和佛罗伦萨的技术协会相比,甚至还超过它们。关于杭州的商会,马可写道:“众多商人云集在这里,他们十分富裕,经营着大宗贸易,没有人能估量出他们的财富。只知道贸易主(他们是企业的头目)和他们的妻子们都不直接从事任何事情,但是,他们过着如此奢侈豪华的生活,以致人们会想象他们是国王。”纸钞的普遍使用便利了商业交流,马可打趣地称纸钞为点金石。“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中国,每个人都乐意接受这些纸币,因为无论他们走到大汗领地内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像使用金子似地毫不困难地用它们来做买卖。”中国人强烈的商业意识也令这位惊诧。他不断地回忆起那些丰富的场面:从印度回来的船只满载着香料——胡椒、生姜和肉桂;或载着稻米的帆船沿长江顺流而下,或沿大运河逆流而上;杭州或泉州的商店内,贵重货物琳琅满目,有生丝、锦锻(很厚的丝织品)和锈花织锦(有金线或银线绣成花的丝织品),以及有特殊图案的缎子,或称“刺桐布”织品。
马可以同样赞赏的语调描述了中国的主要市场:北方丝绸中心是汗八里(北京,每天都有上千辆满载生丝的大车驶入,用它们制成大量的金布和成丝);成都府(四川,成都)生产薄绢,并将这种丝织品出口到中亚;安庆或开封(?)和苏州(江苏省)生产金布;扬州(江苏,扬州)是长江下游的最大的稻米市场。最繁忙的地方是原南宋都城、京师(Quinsai,浙江杭州),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并没有丧失它以往的商业活动。事实上,因为它现在与蒙古大帝国的一切贸易联系起来,商业贸易还获得了发展。马可把它描述成中国的威尼斯。首先是作为最大的食糖市场而提到它。无数的船只把印度和东印度的香料带到杭州,又从杭州把丝织品带到印度和穆斯林世界。于是,杭州城内住着大批阿拉伯移民,以及波斯和基督教的商人们。最后,是福建省内的两个大港口:福州和刺桐(即泉州)。福州商人‘囤积了大量的生姜和良姜,城里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砂糖市场和一个大的珠宝交易市场,这些珠宝是用船从印度群岛捎来的”。
元朝最大的货栈仍要算马可所记的刺桐,“从印度来的所有船只,满载着香料、宝石和珍珠停泊在刺桐,简直难以想象。蛮子[指中国南部]的所有商人们云集在此,它是全中国最大的进口中心。可以说,如果有一艘载着胡椒的船从印度群岛驶往亚历山大港,或者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港口的话,那么,就有一百多艘驶往刺桐。”这些记载得到了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塔的证实,他在1345年左右谈到了刺桐[泉州]。
显然,在蒙古人统治期间,中国市场与印度和马来亚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按马可的陈述,大批中国船只定期在爪哇港停泊,带回“黑胡椒、良姜、毕澄茄、丁香和其他香料,刺桐商人们因经营这些商品而致富”。从另一些史书中,可以了解到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们与特拉万可和卡纳蒂克的大公们缔结了真正的商业贸易协定。中国的商船队载着大捆的生丝、彩色丝织品、缎子、薄绢和金丝锦缎定期在加韦里伯德讷姆,卡亚尔、奎隆和锡兰停泊;返回中国时,运载着印度世界的胡椒、生姜、肉桂、豆蔻、平纹细布和棉布,以及印度洋的珍珠和德干高原的钻石。
此外,元朝大汗的幼支在波斯建立的汗国促使了两国之间的频繁交往。旭烈兀家族的波斯汗们在伊斯兰环境的包围中仍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蒙古人的爱好,他们派人到中国获取诸如丝、瓷器之类的奢侈品,当时的波斯袖珍画像开始显示出中国工匠们的影响。反过来,蒙古人统治下的波斯也把地毯、马具装备、盔甲、青铜器和搪瓷制品输往中国。
最后,马可的游记和佩戈洛蒂(Pegolotti)撰写的《贸易实践》(Pratica della mercatura)都证实了这一点:蒙古征服使中国社会与欧洲发生联系。到13世纪末,贯穿大陆的两条路把欧洲与远东联系起来。第一条路是从钦察汗国到敦煌,对欧洲人来说,它起于克里米亚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业据点,更准确地说,起于顿河河口处的塔那。该道的主要驿站有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即蒙古钦察汗国的都城,接着是锡尔河中游的讹答刺和伊塞克湖以西的怛逻斯和八拉沙衮。从伊塞克湖起,有一条小道进入蒙古,途经叶密立河、也儿的石河上游[黑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到达鄂尔浑河上游的哈拉和林,从哈拉和林该路南通北京。从伊塞克湖西端出发的另一条小道,通伊犁河上游的阿力麻里(固尔扎附近)、别失八里(今济木萨)、哈密和甘肃肃州,然后进入中国本土。第二条路是穿过波斯的蒙古汗国,它的起点或者是特拉布松希腊国都城、黑海边的特拉布松城,或者是从法属叙利亚附近的西里西亚的亚美尼亚国最繁忙的港口刺牙思。无论从哪一个起点,该路都要穿过与波斯的蒙古汗国保持紧密联系的属国、小亚细亚塞尔柱克苏丹国的东境,然后到波斯汗国的实际上的都城桃里寺。从桃里寺起,主要驿站常常是可疾云[加兹温]、刺夷、莫夫[马里]、撒麻耳干[撒马尔罕]、塔什干(当时名柘析)、喀什、库车、吐鲁番、哈密和甘肃。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即从莫夫到巴里黑、巴达克山、喀什、于阗、罗布泊和敦煌。经过这些不同的商路,从远东来的商品被直接运往欧洲。
除了这些与古丝绸之路一致的陆路外,蒙古征服还重新开通了海路,或称香料之路。当阿拉伯人和塞尔柱克人统治的伊朗一直对欧洲实行关闭时,而波斯的蒙古汗们则对要经海路去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们敞开了他们的领土。从报达哈里发朝的灭亡到伊斯兰教在波斯汗国内获得最后胜利的期间,天主教的旅行者们可以从桃里寺到霍尔木兹,畅通无阻地穿过伊朗,然后从霍尔木兹码头乘船去塔纳、奎隆和刺桐。正如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鄂多立克的旅行就是沿这条路线旅行的典型。反过来,来自中国的丝绸和来自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在霍尔木兹卸下,由商旅们带着通过蒙古统治下的波斯到达桃里寺大市场,然后由此分发到基督教世界的港口特拉布松,或者是刺牙思。
必须强调的是,道路所以这样自由畅通是以大屠杀为代价的,是蒙古征服的一大有利的客观后果。中国、突厥斯坦、波斯、俄罗斯团结在一个大帝国之中,在蒙古王公们的统治之下,按严格的札撒进行管理,这些王公们关心商旅的安全,宽容各种信仰,重新开通了自上古末期以来就阻塞不通的世界陆上与海上的大道。而波罗一家的旅行证明了比以马厄斯·梯梯安洛斯一名为标志的旅行大得多的活动。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伊朗与欧洲互相之间开始了真正的接触。这是震惊世界的成吉思汗征服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同样也是幸运的结果。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